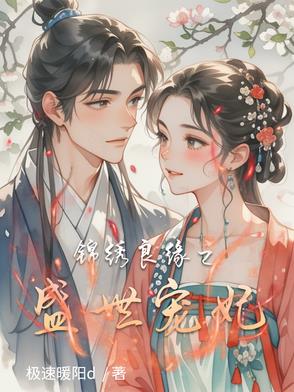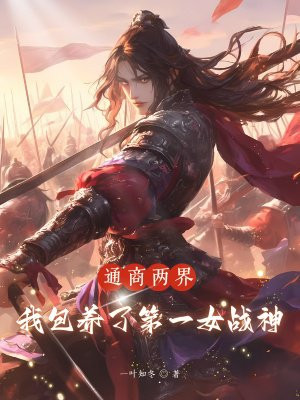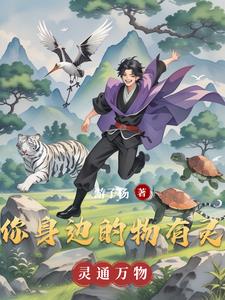63 同道(2/4)
荀贞从前世到现在,从求学读书至今,从没听过这种解释,他楞了会儿,说道:“‘学而时习之’,将‘学’理解成‘学说’,将‘时’理解成‘时代’,将‘习’理解成采用。……,似也有道理,能自圆其说,成一解释。”
他琢磨了片刻,又说道:“如此一来,这三句就不是分裂的,而是连贯一气的了。……,并且这三句话是《论语》开篇之第一段,按此理解,竟是在点名《论语》一书的主旨了,‘我的学说如被时人接受,我将很高兴;如不被时人接受,我也不怨恨’,子贡曰:‘夫子温良恭俭让’,夫子也正是这样的人啊!”
他一门心思思忖,在进了后院的时候,没有注意到院中的树木,险些被枝杈将“冠”勾掉,惊醒回来,扶正了冠帽,拉住荀彧的衣袖,又问了一遍:“文若,你这个朋友是谁?”
这个“新的解释”令人耳目一新,绝非死读书的人能够想到的,非得思维与众不同者,也就是“不走寻常路”的人,或者就是说:只有“奇才”才有可能想出来。重点已不是这三句话的本意到底是什么,而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,而是“到底是谁竟能想出这层意思”?
荀彧笑道:“子曰:‘君子,不重则不威’。先前出门来拜见家君时,四兄忘带帻巾;今闻鄙友言论,又拽我衣袖。四兄,你我见面虽不多,但我久知你是一个稳重少语的人,今日为何接连失态?”不动声色地将衣袖从荀贞的手中抽出。
荀贞也发现了自己的失态,不过他并没有不好意思,而是哈哈一笑,说道:“忘带帻巾,是因为敬重;拽你衣袖,是因为心急。”
“为何而急?”
“‘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’?”
两人相对而笑。荀贞第三次问道:“请问尊友何人?”
“阳翟戏忠。”
戏忠是谁?荀贞不知道,但他知道另外一人,也是姓“戏”,而且就印象中来说,似乎整个汉末三国就这一个姓“戏”的,并且刚好这个人也是阳翟人。他迫不及待地问道:“可是戏志才?”
“咦?四兄也知此人名字么?”
荀贞欣喜难掩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,只能连连说道:“曾有耳闻、曾有耳闻。”
荀彧站定脚步,诚恳地
本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>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