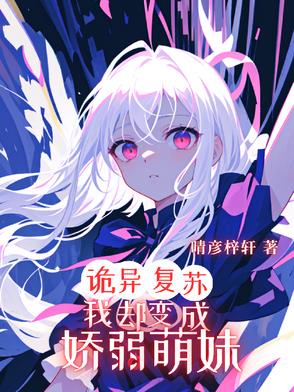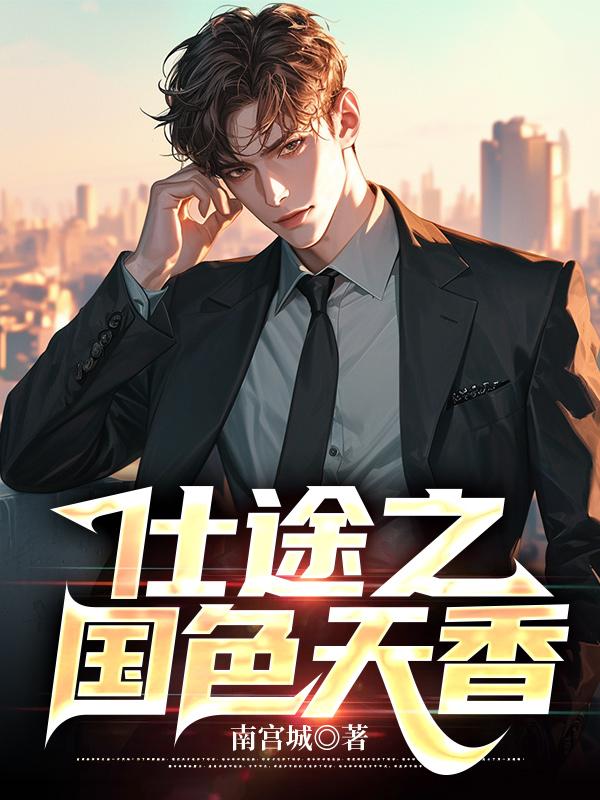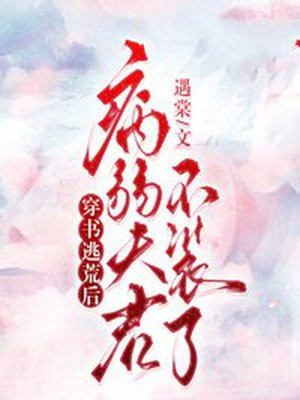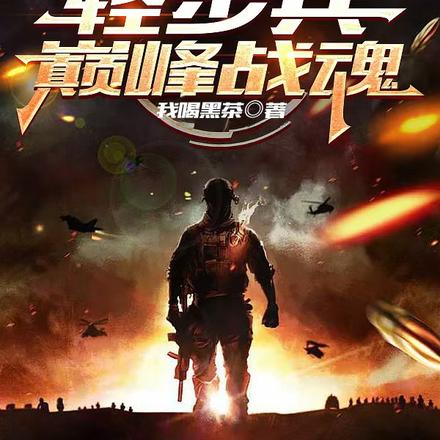第80章 这个时代的光(3/5)
的田埂、挤进老祠堂、坐上冷板凳。
他们不看“文件”,只看“流程”。
不问“成功经验”,只问“失败怎么处理”。
而蜂窝制度,偏偏最擅长给他们“看失败”。
有位东南亚治理学者看完“失败制度留存墙”,感叹道:
“你们不是把制度失败当耻辱,而是当作制度的发育过程。”
“这太先进了。”
可陈鹏飞却淡淡摇头:“不是先进,是实在。”
“我们不是学者,是活在制度里的老百姓。”
“我们允许自己写错,因为我们承担得起。”
“我们不怕出错,因为我们随时准备改。”
……
与此同时,蜂窝平台的“田埂对话”功能继续扩大。
越来越多的村庄,将日常争议录音、意见冲突甚至代表互怼的会场音频上传——
有的吵得惊天动地,有的哭了,有的砸了板凳,也有的会后一起喝酒说“下次咱重新议”。
平台不删、不剪、不裁,只做一件事:
在每条录音末尾附上一句话:
“制度,从来不是写出来的,是吵出来的。”
而就在全网热议蜂窝制度时,一个意想不到的节点降临了。
教育部发出通知:蜂窝制度演化过程、制度公议结构、制度失败档案机制,将作为高一“思想政治”课程新增教学模块,列入2026年秋季新版教科书。
这意味着,蜂窝制度,不再只是“实验”,不再只是“地方现象”,而是——
走进了课堂。
走进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的世界里。
“制度”不再是遥远的中央文件,而是“我爷爷参与写的共田规章”、“我妈昨天开会吵赢的红利议案”。
那一刻,蜂窝平台真正感受到什么叫“制度意识觉醒”。
制度,不再是管理手段,不再是干部职责,不再是“能人策划”。
它成了村里人,“身份的一部分”。
就像你会说“我姓王,我是陕西人”,现在他们也会说:
“我家有一条制度,是我写的。”
本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>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