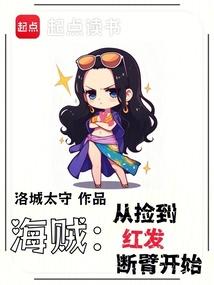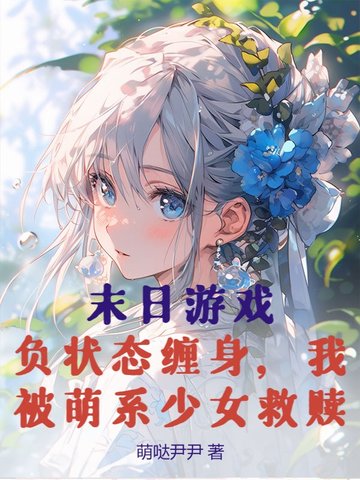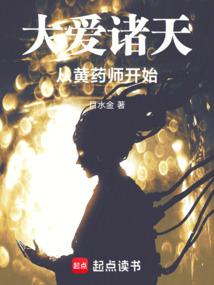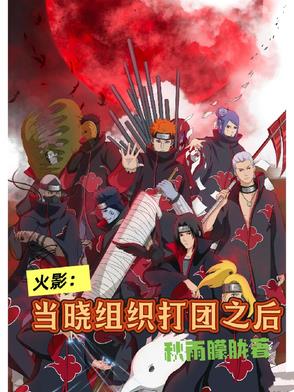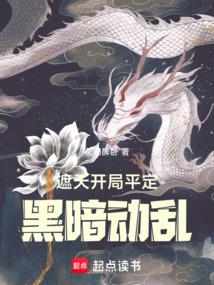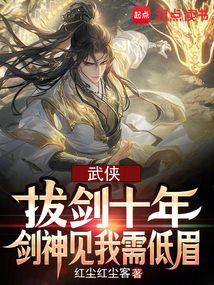第5章 才女与神童(3/5)
后,姑侄俩交换了眼神,皆想:这诗从未见过,但就诗意判断,当是半山居士的手笔,西山小神童定是拿祖父的旧作敷衍了事了。
二人自以为事实便是如此,却也不说破,毕竟人家纵算是抄袭也是抄自家人的。
他们却不晓得王棣此刻正暗自嘀咕:板桥先生莫怪莫怪,剽窃是不对的。
前世作为文科生的他甚爱唐诗宋词,很是熟背了不少名篇佳作,咏竹诗中最爱的便是郑板桥的这首《竹石》,咏物言志嘛,此诗最能表现刚烈坚贞、高风亮节。是以,苏小妹以竹为题,他想都没想便随口念了此诗,倒真无做文抄公之心。自然,也不能多加解释,越描越黑罢了,却没想到这姑侄俩会以为自己拿了王安石不曾问世的诗作来充门面。
果然,竹荫石径尽头有一左一右两座茶亭,各有石桌石凳若干,左边亭子里数位士子装束的人正在高谈阔论,见了王棣一行,虽然都尚年少,但穿着气度不凡,且有侍婢随从跟伴,不由多看了几眼。
早有侍婢摆出水果茶点,侍奉三位小郎君、小娘子休憩。
王棣瞄了瞄对面亭子,面生的紧,想必尽是寂寂无名的士人——道理很简单,王安石寓居半山数年,来访者无数,江宁一地稍有名气的文人悉数登临。抛却王半山的政治主张不提,其且是当世文宗,能得其稍加提携,名望定必大涨。
那数位皆着襕衫,头上簪花。
彼时,男士簪花并不算另类奇怪的妆扮,其受众之广,从朝廷官员到平民百姓,已俨然成为一种社会风俗。
苏轼便曾诗曰:“人老簪花不自羞,花应羞上老人头。醉归扶路人应笑,十里珠帘半上钩。”
而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率淮南。一日,后园中有芍药一干分四歧,歧各一花,上下红,中间黄蕊间之。当时扬州芍药,未有此一品,今谓之“金缠腰”者是也。公异之,开一会,欲招四客以赏之,以应四花之瑞。时王歧公为大理寺评事通判,王荆公为大理评事签判,皆召之,尚少一客,以判钤辖诸司使忘其名官最长,遂取以充数。明日早衙,钤辖者申状暴泻不止,尚少一客,命取过客历,求一朝官足之。过客中无朝官,唯有陈秀公时为大理寺丞,遂命同会。至中筵,剪四花,四客各簪一枝,甚为盛集。后三十
本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>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