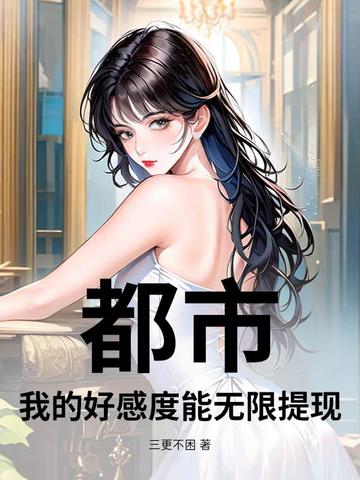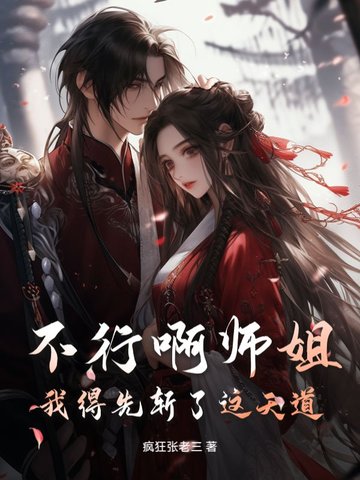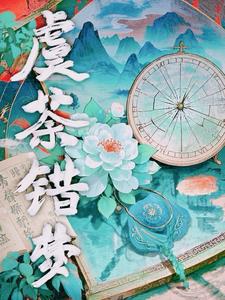第52章 夏国王汴京留客,许芳丛千堆(3)(3/8)
这个问题非常尖锐,李秉藏却如此作答“前生所致,前世所为,吾等半生戎马皆为赴前人雄志,然而到头来却发现身前身后之薄名不过是一场云烟。宋人之血为我所流,若是想索命,尽可过来,吾等没有半点怨言,毕竟败军之将能成为诸位座上宾已然是吾之荣焉,何必再惋惜这三尺之躯。至于坦然,从何言之,这也许就是宋人和夏人的区别,宋人惜命,人人皆贵;夏人不惜命,人人皆轻,王公贵胄哪会在乎人间生死,吾亦是如此,现在既失王命,就也如世间蝼蚁,命不值三分。”
张耒冷笑道“王公贵胄为何不在乎他人性命,这与禽兽何异?”
苏轼急忙阻止张耒言语“唉!文潜莫要多言,今日青山王乃是吾等上宾,何必一一审问之,搞得此局如大理寺断案一般。”
李秉藏急言“莫妨,今日论政,可论天地万物,百无禁忌,也正好让我对前生作一个了结。”
张耒用眼神示意苏轼,然后又接着问曰“宋人言,众生万物皆是平等,官家亦是取消了前朝的天子之说,民可反对官,臣可反对君,这是宋人之利,可是夏人还是沿用前唐旧例,视百姓如草芥,善征伐于天地,此种愚弄苍生之策是否符合夏人福祉?”
李秉藏回曰“夏人本居天山与大漠之间,黄沙漫天,水草不足,只能逐水草而居,春时修整,夏时西去,秋时放牧,冬时就得归来(回兴庆府),否则就会饿死在山间水侧,牛羊之肉搁不过三月,不似宋之舂米,荞麦可存数年。饿了就要掠食,渴了就要抢水源,与其抢自己的,不如抢宋人的。此既可解决温饱,又可激夏人志气,何乐而不为呢!究其原因,乃是天命所致,宋人得地便宜而夏人获地蛮荒,并非夏人生来善于征伐。至于唐例,我夏人本就是前唐靖难军,奉唐所宗,自然要依唐例。所以夏人之福祉乃是吃饱不饿,而宋人之福祉早已经逾越此阶层也,宋人便更关心诗词歌赋,华服彩章。这是夏人所望尘莫及的。”
苏辙道“世间物资分布本就有高低不同,如果因为获取的少,就行劫掠,确实有违天理,尘世难容。”
李秉藏道“茫茫大漠之上,哪里有天理可言,存活才是王道!吾曾三更起,打造兵器,修炼武功,就是为了能习得非凡的本领,在劫掠中能抢的头功。西夏的王虽然
本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>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