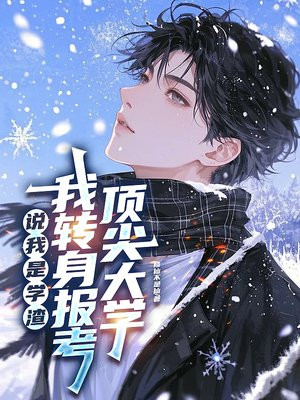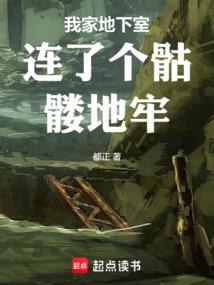第4章 历下汴京两地长,苏门各尽觞(16/27)
。有人酒意临头,遂闲话起来“苏翁今此归来,吾等方有引路,目今朝中乱局唯有苏翁可以按顺,此乃大宋之福也。”
苏轼起身长叹“大宋乱局,乃新旧之争久矣,各方势力相互倾轧,新旧实力又齐虎相当,怨怒和忧愁积压,苏某恐难掘动各方势力。”
黄庭坚闻言说道“苏翁离朝久矣,素不知朝中之局,乱中有稳,稳中亦有因果,新旧势力处于平衡,苏翁即不偏向何方,只需引吾等走入新的道途,新旧之力皆不可破,若一方破之,则另一方得势,吾等必不可与得势一方争持,吾力尚轻,难以为继。为今之计,不破而立新才为稳妥。”
苏轼道“不破旧局而立新局,这倒是一个新颖的办法。”
秦观又言“朝中之所以无以进之,亦因为新旧之力平衡,相互掣肘,吾等力微,不足以撼动,吾与文叔兄,鲁直兄等兜兜转转不过是在为苏翁归来拖延时间罢了。根本谈不上有何种建树。”
苏轼听闻李文叔之名,遂生迟疑“李文叔?此人许久未见,其在何处?”其时苏轼闻李格非之名已久,但是并未与之深交。在御史台案之前苏轼大概也就和李格非有数面之缘,因其是韩琦的门生,这互相之间就不好怎么交割了,毕竟门第有别,互相交际恐有不便呀!后李格非因一篇《王公祭志》而入宰,随之便名扬天下,苏轼才算真正注意到李格非这人。
张耒补充道“李文叔为新任尚书右仆射,学术成就非凡。然则朝中既无党羽,亦无后盾,揪揪行事,亦如蹒行,其本人常以苏子门生自居。吾观此人行为得体,为人正派,吾等可纳其为忠志之士,免其为新旧之人所利用。”
苏轼听闻然也“李格非似曾有所交集,也就数面之缘,其文章吾读之亦有大气磅礴之势。只是当时他娶了王拱辰的孙女,我以为他会一心扑向王家怀抱。如今王门势颓,不知其心属何地?”
晁补之对道“苏翁且知王拱辰已去矣,其子王贺之为新党激进者,年少鲁莽,目前已经罚官去职,另一子王苑之,即李格非的岳父,其人在朝中成就不大,亦多有隐退之意,其本人并无明确新旧意向。吾观王苑之则更想明哲保身,远离朝局,退而安居,王门则难成气候,李格非即为孤胆一人。目前其行为举止多倾向于吾等,不可失之呀!”
本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>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