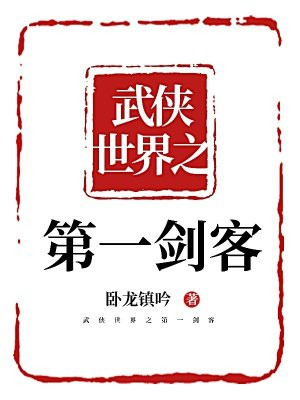第19章 毫香雪祭(2/2)
树,枝桠上积着厚雪,却在顶端挑着几星嫩芽,像是雪地里开的小灯。“别瞧这雪压着,等开了春,根底下吸饱了深海泥和花粉,芽头能比往年长半寸。”他说话时,指尖不小心蹭到竹篓里的茶青,白毫沾在手套上,像落了层细雪,竟比外头的雪还要白上几分。
黄昏收工时,茶寮里飘起了姜汤的热气。沈青禾把最后一篓茶青搬进烘房,竹匾上的芽头还沾着未化的雪粒,白毫凝着水珠,在火塘的光里闪闪发亮。阿顺伯往火塘里添了块松木,火星子蹦起来,映着墙上挂的茶经,忽然长叹一声:“早年咱不懂,总想着催芽施肥,倒把茶树逼得没了魂。如今跟着陆先生养地,又遇着这毫香雪,才知道茶跟人似的,得顺着天时地利,急不得。”
雪还在下,却渐渐转成了细霰。苏明月趴在窗台上,看雪光里的茶田像幅淡墨画,新施的深海泥在雪下泛着微光,母茶树旁的花粉印子,竟隐隐连成了枝桠的形状。他忽然想起沈从文写过的:“一切自然美都像是为了人的眼睛而生成,人的眼睛却又为了自然美的不断变化而生成。”此刻的政和茶山,不正是自然与人的眼睛、手和心,共同酿成的一首诗么?
夜深时,沈青禾提着灯去看茶青,雪光透过窗纸,把烘房映得青白。竹匾里的芽头不知何时舒展了些,白毫上的雪粒化了,却留下层薄薄的水痕,像是被谁吻过似的。她忽然笑了,想起白天撒深海泥时,雪花落在泥粒上,竟腾起阵细雾,那雾气里有海的腥咸,也有茶的清甘——原来山与海的缘分,早就在这毫香雪里,酿成了茶灵的苏醒。
雪整整下了三日,等初晴时,茶山上的老茶树竟齐刷刷地冒出了新芽。那些沾过毫香雪、吸了深海泥、得了母树花粉的芽头,白毫密得像羊羔的绒毛,在阳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。茶农们都说,这是茶树在谢雪,谢海,谢那些懂得等、懂得敬的手。而沈青禾知道,这漫山的白毫,终究会变成春天里最清亮的茶汤,就像沈从文笔下的沱江,不管流过多少弯,终究会带着故土的味道,流向远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