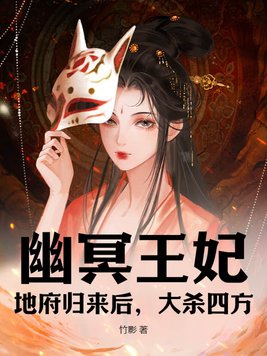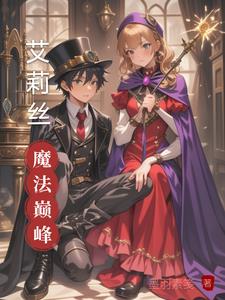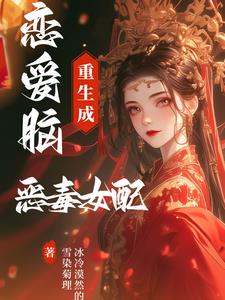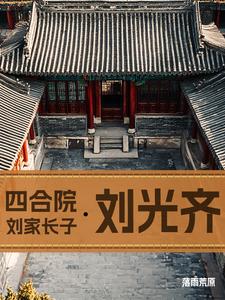第五编:隋唐佛学(18/24)
之所谓传法意义大不同。兹举《续僧传》所载三数事以辨明:
(一)《法敏传》载,兴皇法朗将死,与门徒言后事,令推举一人继主讲座,所举悉不当意,乃自举茅山明法师,众人骇异,私议法师他力扶矣。及明法师就讲座,叙十科义,大众惬服,称为“兴皇遗嘱”。又《道庄传》载,庄学成实于彭城琼法师,琼因年疾“特欲传绪,通召学徒,宗猷顾命”。众人属望于庄,琼言“恐其徙辙余宗”,后庄果从兴皇法朗学大乘四论。据此二事可见其时讲座继续之情形。
(二)《智琚传》载,智琚遍学经论,从师甚多,自谓“学无常师”。尝听坦法师讲《释论》,及坦将逝,以五部大经付嘱,后琚亦常以之敷讲。琚将死,又以《华严》《大品》《涅槃》《释论》四部义疏付嘱其入室弟子法衍。
(三)《法恭传》载,“听余杭宠公讲《成实》,屺公《毗昙》,逮宠将亡,乃以麈尾付嘱,……恭既受法寄,相续弘持”。
“遗嘱”“付嘱”,本出于佛经,吉藏《法华经义疏》卷十一《嘱累品》释曰:“嘱累有二,一以法付人,二以人付人。”据上引三条,唐代前所谓付法者,盖指可继续其师讲经论之僧人,所付者为经论之讲解或所著述之义疏,至或以麈尾付嘱以为象征。
“付法”一词,至隋唐天台宗、禅宗等兴起之时,实含有新义:一则立宗者自称其继承佛之正统,常引《付法藏传》以证明。如时有疑《唯识》《摄大乘论》《法华经论》是否可信,吉藏释曰此三书作者天亲于付法藏中有其人,是故可信(见吉藏《法华玄论》卷四)。天台宗传授史则是据龙树为付法藏第十三人。禅宗传授史亦据《付法藏传》《萨婆多传》等。再则因禅定盛行之影响,传法遂有神秘之意义,与名相解释之学不同。天台特重因禅发慧,智诣慧思受业心观,得法华三昧,思曰:“非汝莫感,非我莫识。”而禅宗顿教,更是以心传心,秘密相传,不著一字,其后参禅棒喝,皆为其顿悟学说之体现。此与前之讲习之学,读经说法,以之相传,大不相同也。
传法概念之形成,与宗派之兴起有关,而宗派形成之原因甚为复杂,须具体研究。如鸠摩罗什传大乘空宗之学,佛陀跋陀罗传一切有部之禅法,法自不同。在长安时,有姚兴、姚显、僧略、僧
本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>>>